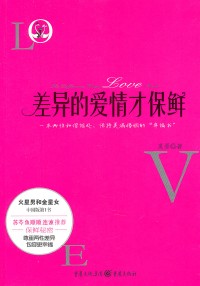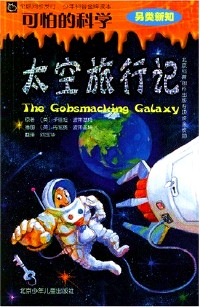共找到 33 项 “和金星” 相关结果
- 全部分类
- 全部
- 文学
- 历史
- 哲学/宗教
- 法律
- 政治/社会
- 医学
- 教育/心理学
- 艺术/传媒
- 研究生考试
- 资格认证考试
- 公开课
- 语言
- 经济金融
- 管理学
- IT/计算机
- 自然科学
- 工学/工程
- 体育
- 行业资料
- 音乐
- 汽车机械制造
- 文档模板
- 创业
- 农学
- 生活
- 数据库教程
- 民族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简介: 本书是国际知名情感专家约翰?格雷博士《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 星》系列之三。 在本书中,约翰?格雷博士从火星人和金星人的天然差异入手,分析了 男女双方在性爱上的种种问题―― 男人是蓝色的,喜欢冷静和沉默;女人是粉色的,喜欢表达和倾诉; 男人看重的是性爱的快乐,女人注重的是爱情的浪漫; 男人为性而爱,女人为爱而性; 男人好比喷灯,激情和兴趣来势凶猛,去势匆匆;女人则如火炉,看似 温吞之水,却会愈演愈烈; ……
作者: (美)格雷 著,刘增莉 译
简介: 本书是国际知名情感专家约翰·格雷博士《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系列之三。在本书中,约翰·格雷博士从火星人和金星人的天然差异入手,分析了男女双方在性爱上的种种问题—— 男人是蓝色的,喜欢冷静和沉默;女人是粉色的,喜欢表达和倾诉; 男人看重的是性爱的快乐,女人注重的是爱情的浪漫; 男人为性而爱,女人为爱而性; 男人好比喷灯,激情和兴趣来势凶猛,去势匆匆;女人则如火炉,看似温吞之水,却会愈演愈烈; ……
Why men are from mars & women are from venus
出版社: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
简介: 在现代社会,为了解决生计问题,男人和女人都要应对巨大的工作压 力。当回到家里时,就会因为太忙或太累,而不能好好处理自己的感情问 题。他们经常会感到自己遭到忽视或冷落,和伴侣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很容易就发生冲突。只要善于沟通,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变得 更加亲近。但是男人和女人似乎是来自完全不同的星球: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由于不了解对方处理压力的方式,导致了火星人和金星人 因沟通困难而战争不断。 本书将从生理、心理等各个方面分析造成男女处理压力方式不同的根 本原因,告诉读者为什么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同时,会帮助你 找到有效处理自身压力以及帮助伴侣消除压力的新途径。不管你是未婚, 还是已经成家,都能够在本书中找到一系列新颖实用的方法,它们可以改 善你和伴侣的交流方式,使你和伴侣更加和睦,让你们享受到一生的浪漫 与恩爱。
作者: (美)约翰·格雷(John Gray)著;苏元[等]译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简介:《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系列,风靡全球的心理自助读物,畅销1.4亿册。 火星人金星人 长相厮守:男女持续爱恋的秘诀。 永远的距离,永远的爱人,2007年修订版。 解密两性情感密码,长踞《纽约报书评》畅销书排行榜。 亚马逊网上评论 约翰·格雷在帮助整个美国!如果每一对夫妻都阅读此书的话,离婚率将会直线下降。正如《今日美国》文章所称:火星人与金星人的形象已深入并改变着美国人的生活。 这本书做了一项非常伟大的工作,不仅告诉了你男人和女人在思想模式、做事程序、交流方式上都非常不一样,而且给出了克服交流障碍的有效方法。当男人和女人之间变成很亲密的夫妻关系时,更需要意识到双方的心理差别和相互尊重对方的自然需求、期望和梦想。 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男人和女人明明用同样的语言,说同样的词汇和句子,但他们各自想表达的意思却如此不同。这书就像一本两性用语词典,帮我们做了很多“翻译”的工作。它使我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观察男人和女人,写得非常幽默,的确太棒了! 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心理自助读物,当我读到一半的时候,妻子问我怎么样。我唯一的反应就是这本书没把我们的名字写对。我简直不敢相信格雷博士是如此准确地描述了我和我妻子这将近37年的经历和对话。 这本书太神奇了,几乎解释了我以前和先生经历的每一次分歧和冲突。读完这本书,我才深刻地理解为什么我的第一次婚姻走向了灭亡,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理解对方的需要。 约翰·格雷让我们知道男人和女人是来自于不同星球的,男女之间在心理情感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火星人和金星人的形象已经永远留存在我们生活的词典里了。
Mars and venus in the bedroom:a guide to lasting romance and passion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简介:☆《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系列 ☆《纽约时报》畅销书第一名 ☆探讨如何从身体和精神方面达到完美与和谐的性生活 本书献给那些忠诚于一夫一妻制的人们。 男人需要性,女人需要浪漫。 男人进卧室向左,女人进卧室向右。 男人先有性后才有爱,而女人则是先有爱后才有性。 只有通过性,男人能才敞开心扉,感受爱情并产生渴望。 很多时候,我们的伴侣似乎来自于不同的星球,他就像来自于火星,她就像来自于金星。进入卧室,火星人和金星人,男人和女人就会截然不同。可惜,人们似乎还没意识到男女之间的差别会如此之大。只有理解和接受男女之间的这些不同,明显的也罢,不明显的也罢,我们才能真正地亲密无间,创造完美性爱。 内容导读 本书从身体和精神方面探讨性生活如何达到完美与和谐。男人会因为女人理解而心存感激,女人自己也会在卧室内外变得更加快乐。 本书在前11章中,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在床上创造完美的性爱。接下来在第12章中,我们将探讨卧室外的浪漫对保持激情的重要性。 十分常见的一种情况是,在结婚几年后,夫妻中的一方不再需要性爱。虽然他/她觉得对方只是失去了对性爱的兴趣,但是,真正的原因却在于他/她在某种情况下不能满足伴侣的性爱需求。通过《男人进卧室向左,女人进卧室向左》一书,我们将从细节上讨论这些不同的需求。 这本书没有太多的技术,还算比较有趣。作者个人倾向于把本书中的很多章节写的简短一些,这样你可随时把书放到一边,尽享这些新的卧室技巧所带来的快乐。
Trapping love by constellation
作者: 静电鱼著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
简介: 金星与太阳的互动,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爱情人格呢? 本书从太阳和金星两大行星出发,详细解析了由太阳星座与金星星座 组合产生的60种搭配星座男的恋爱程序设计、日常感情的喜好兴趣、情感 反应机制与防御机制等各种模式,让每个女性了解到该如何面对各种不同 星座的男性,恋爱中遇到问题时该如何处理。让每个星座男人都能从中找 到属于自己独特的性格介绍,并由此真正了解自己的性格特点,找到最佳 的行为模式,学会正确使用自己的性格。真正把握爱情攻略,才会真正获 得自己想要的幸福。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
简介: 本书是国际知名情感专家约翰·格雷继《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2》之后的又一力作。 在本书中,格雷博士从火星人和金星人的天然差异入手,分析男女之间不同的心理以及行为变化,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恋爱技巧,用于指导那些正在苦苦寻觅自己另一半与永恒爱情的人们。无数人从此书中受益匪浅,有情人终成眷属。愿这本书也能够对此刻正在爱情中彷徨无措的你有所帮助—— 只因孤单寂寞,就降低择偶标准的话,我们就不会吸引到最适合自己的人。 爱情好比播下一粒种子,如果你每天都挖开它看看发芽没有,那么反而会让它死去。 亲密的肉体关系并不代表一切,有时候,发生性关系可能仅仅是一时激情的结果,什么也代表不了,感情必须经历时间的考验才能与日俱增。 求婚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值得珍藏的记忆。
作者: 和金星 著
简介:浅绛是中国山水画的一种技法,为元代画家黄公望所创。清末,景德镇瓷画师们把这种技法运用到了瓷画中,并延伸到花鸟、人物的创作中,逐渐发展成为自成一体的瓷画艺术门类,后人就把它称为浅绛彩瓷。浅绛彩瓷画多是以古代文入画和海派画家的画为蓝本的,因此常书有“仿某人画法”、“抚某人笔意”等语。如“仿元人之法”、“仿华秋岳法”、“抚八大山人笔意”等。从清末到民国初,浅绛彩瓷在中国瓷器史上活跃了60多年,给今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浅绛彩瓷由御窑厂的画师们发端,一开始就成为中国文人雅强。舞燕劳闲阶级的雅玩,受到热烈追捧,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等大师们的作品在当时就非常珍贵。后来有大量画师、匠人投入到浅绛彩的创作中,作品水平参差不齐、匠气日重,最终致使该创作走到了尽头。 浅绛彩瓷壶仅仅是瓷壶大家庭里的一员,在它之前的青花、粉彩、色釉等瓷壶不乏高贵、华丽、精美,特别是官窑壶,价值连城。在它之后的新粉彩瓷壶,因有“珠山八友”及王步等人的天才创作,又出现了瓷壶艺术的高峰。但浅绛彩瓷壶用自己的艺术特质打动了许多人,许多人为之倾倒。我就是这许多人中的一员,十多年来,执着地热爱浅绛彩瓷壶,偶有所得,便心潮澎湃,反复把玩,爱不释手,几近痴迷。虽不曾拥有大师级的作品,但那些二流名家的作品已足以让我陶醉。
Galileo’s Daughter:A Historical Memoir of Science, Faith, and Love
作者: (美)达娃·索贝尔(Dava Sobel)著;谢延光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简介:声名赫赫的父亲大人: 您所钟爱的妹妹——我们亲爱的姑姑的去世,使我们痛不欲生;但同我们对您的关心比较起来,我们因失去她而感到的悲伤就显得毫不足道了。现在,您在您的世界里真的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因此您的痛苦将会更加巨大。既然您最钟爱的人已离您而去,我们惟一能够想象得到的,就是您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完全意想不到的打击承受了多么严峻的考验。当我们对您说我们和您一样深深地感到悲痛时,您不妨想一想人间普遍的苦难状况,也许可以从中得到甚至更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全都是这世界上的匆匆过客,不久都将前往我们在天国的家园,只有那里才有完全的幸福,而我们也必须相信,您的妹妹的幸福的灵魂已经去了那里。因此,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恳求您,大人,去寻求上帝的安慰,把自己交给上帝吧,因为您十分了解,那是上帝对您的要求;如果不那样做就会使您受到伤害,同时也会使我们感到痛苦,因为如果我们听说您在忧愁烦恼,我们会非常难过: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作为我们的美德典范的,除了您,再也没有其他的人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们只有真心诚意地、热烈地祈求上帝给您以安慰,愿上帝永远与您同在,并用我们炽热的爱向您致以,深情的问候。 1623年5月10日寄自圣马泰奥。 深深爱您的女儿, 修女玛丽亚·切莱斯特 维尔吉尼娅和利维亚都不知道她们何时才能见到她们的兄弟温琴齐奥。至少在目前,伽利略觉得最好还是让这个仍在蹒跚学步的小男孩同玛丽娜一起留在帕多瓦。 伽利略离开威尼斯后不久,玛丽娜就嫁给了一个和她的社会地位差不多的体面公民乔万尼·巴尔托卢奇。伽利略不但同意他们的婚姻,而且还帮助巴尔托卢奇在他的一个富裕的帕多瓦朋友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伽利略仍然寄钱给玛丽娜作为温琴齐奥的生活费,而巴尔托卢奇则向伽利略供应望远镜上的镜片毛坯,这些货都是从威尼斯航道内的穆拉诺岛上著名的玻璃厂那里弄到的,这个货源一直维持到佛罗伦萨被证明是一个甚至更好的纯净玻璃供应地为止。 伽利略在佛罗伦萨租了一间房子,这房子“有高高的平屋顶,在上面可以看见整个天空”,他可以在这屋顶上观察天象,安装研磨透镜的车床。在等待交房期间,他同他的母亲和两个小女孩在一起住了几个月,他们住的房间是他向他的妹妹维尔吉尼娅和妹夫贝内代托·兰杜奇租来的。尽管不久前发生了一些法律纠纷,伽利略的亲属们还是为他提供了一种相当温馨的家庭环境,不过,“这个城市冬天的有害空气”却使他不胜其苦。 “在离别了这么多年之后,”伽利略叹息说,“我又碰到了佛罗伦萨的这种稀薄的空气,它是我的头和身体的其余部分的一个残忍的敌人。在最近的这3个月中,感冒、出血和便秘使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变得虚弱和萎靡不振,实际上我一直是在家闭门不出,或者更确切地说,卧病在床,但又没福睡上一觉,也无法得到休息。” 在健康许可的情况下,他把时间用来研究土星问题。土星是一个比木星远得多的行星,其距离显然已到了他的最好的望远镜的分辨率的极限。他想他看到了土星的两个大而固定的卫星。他用一个变换了字母顺序的拉丁短语来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如果把这个短语的字母顺序正确地还原,它的意思就是:“我看到了一颗最远的有3个身体的行星。”为了在这个新发现在获得适当的证实之前宣布这是他的发现而又不致贻笑于人,他迅即派人将这个拉丁短语送给几个著名的天文学家。然而,他们当中竟没有一个人能将其正确地破译。在布拉格,伟大的开普 勒这时虽然已有望远镜在手并认为它“比象征君主权位的权杖都要宝贵”,但他也错误地理解了这个信息,以为那是说伽利略发现了火星的两颗卫星。 在1610年整个秋天,随着金星在夜空中出现,伽利略对这颗行星的大小和形状变化进行了研究。他还把一架望远镜始终对准木星,为弄清楚这4颗新卫星准确的轨道运行周期而长期奋斗,以便进一步证实它们的实际情况。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天文学家抱怨说,为了用那些劣等的仪器看到木星的那几颗卫星,他们已经用尽了力气,但仍一无所获,因此,他们对这些天体是否存在表示怀疑。尽管有开普勒的支持,但还是有人恶意中伤说,那些卫星十有八九是错视,说不定就是伽利略的透镜把它们弄到天上去的。 既然这几颗卫星成了佛罗伦萨大公国有争议的问题,那就必须对这一局面立即予以补救,以保护大公的荣誉。伽利略匆匆忙忙地尽其所能制造了许多望远镜,不但用来供应全意大利的王公贵族,而且还出口法国、西班牙、英国、波兰和奥地利。“为了维护和提高这些发现的声誉,”伽利略论证说,“我以为似乎有必要……通过效果本身来使尽可能多的人看到真相、承认真相。” 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包括伽利略以前在比萨的一些同事,拒绝用望远镜去看亚里士多德的永恒宇宙中这些所谓的新东西。伽利略用幽默的语调把他们的诋毁挡了回去:1610年12月,在获悉一个这样的对手去世时,他大声地表示希望,这位教授尽管在世时对梅迪契星不屑一顾,但如今在前往天堂途中可能要碰上它们了。 为了巩固自己第一个宣布这一发现的地位,伽利略觉得,到罗马这个不朽之城去广为宣传他的发现,乃是明智之举。在这之前,为了同杰出的耶稣会数学家克里斯托夫·克拉维乌斯讨论几何学问题,他曾于1587年去过罗马一次。克拉维乌斯就天文学问题撰写过一些颇具影响的评论,因此他现在肯定会欢迎关于伽利略最近工作的消息的。科西莫大公没有反对这次旅行。他认为这可以提高自己在罗马的身份,因为他的兄弟卡洛当时正担任梅迪契家族驻罗马红衣主教这一传统职位。 伽利略在1618年秋天长时间地抵抗了诱惑,不到户外去看看这三颗彗星中的任何一颗,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既然他觉得身体很好可以与到访者进行学术性讨论时也仍然如此, 这就尤其令人难以置信了。但事实是,11月份夜晚的空气对他来说有着可怕的危险,他毕竟是一个50好几的人了,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与一个又一个疾病的斗争中度过的。此外,伽利略从他的朋友们的叙述中无疑知道,即使他为了亲自研究这些物体而甘冒生命危险,他也不一定会看到很多情况。尽管借助最高倍的望远镜,彗星或“多毛星”的轮廓也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当望远镜滤掉恒星的光线时,恒星就变成了光点;如果对行星做同样处理,行星就变成了小小的圆球。彗星则与恒星或行星不同,它不可能清晰地聚焦。而伽利略之所以踌躇不前,是因为他认为彗星是地球大气的一部分——这一次他倒是和与他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意见一致了,只是理由不同罢了。 伽利略就这样地否定了他的丹麦前辈第谷·布拉赫的发现,因为第谷曾在1577年观测过一颗大彗星,在1585年又观测了另一颗彗星。第谷大概是世界上最能干的用肉眼观测天体的人,他每天晚上用他那超大的测量仪器跟踪观测那颗彗星以确定它的方位。他通过对方位的研究发现它比月亮远,也许和金星一样远,而对于16世纪的思维方式来说,这意味着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或者那颗彗星是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晶状天体中撞毁的,或者这些天体是不存在的。第谷由于是这方面的第一个欧洲人而胆子很大,所以他在1572年选择了后一种设想来鉴定一颗新星,这使他深信变化是能够在永恒不变的天空中发生的。 伽利略由于在1604年亲眼目睹了第二颗新星,所以他支持已故的第谷对这颗新星的性质和重要性所作的说明。但他却看不起第谷的行星体系,认为那是托勒密和哥白尼之间拙劣的折衷方案。至于第谷十分仔细地跟踪观测的那颗彗星,伽利略也对之不屑一顾,认为那不过是一个虚幻的目标而已。他把彗星看作是空气中异常的发光现象——极有可能是高空水汽对阳光的反射——而不是天体本身。伽利略认为,你无法测定一颗彗星的距离,就像你无法捉住彩虹或控制北极光一样。 于是,第一天像开幕一样开始了,几个人物已经聚集在一起,他们的交谈立刻进入了正题。这一天的讨论在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和哥白尼的世界观之间划定了界线。为此,辛普利奇奥提出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地球根本不同于所有天体——因为地球是由元素而不是由以太构成的。伽利略的化身萨尔维亚蒂试图为地球在天空找到一个位置。而萨格雷多则憨厚地赋予地球——“宇宙的渣滓、藏垢纳污之地”——以一种由其自身特有的易变性所产生的独一无二的力量:“就我而言,我认为地球是非常崇高伟大而令人钦佩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地球上不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修改、变化和生成等等。如果地球不经历任何变化,它就会是一个浩瀚的沙漠或一座碧玉之山;或者,在洪水时期淹没它的大片的水结成了冰,使它成了一个万物不生、永无变化的巨大冰球,那么我就应该认为它是宇宙中一块死寂一片的毫无价值的东西,总之,是一个多余的、本质上不存在的东西。” 关于太阳如何通过黑子爆发并围绕太阳腰身一圈圈缩小而同样发生变化这一点,萨尔维亚蒂用他们的“朋友”的望远镜得来的证据来对他表示支持。他提出,月亮和所有星星,无论是固定的或是移动的,也可能都在变化,不过这种变化迄今没有发现罢了。亚里士多德认为,永恒不变是完美天体的规定属性,这种说法在这里完全变成了孤陋寡闻。 ……
出版社: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
简介:《金星女火星男为什么会相撞:一辈子不再争吵的秘密》 作者约翰•格雷博士,是研究两性关系的著名专家,他深刻的理论和洞见改善了无数伴侣的情感关系。他在本书中为火星人和金星人提供了最有价值的信息,告诉他们如何“武装”起来,一生一世和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在书中指出,对于日常压力,男人和女人通常会产生怎样的误解;他们为什么习惯于以错误的方式处理这些压力;还有,他们各自做出的反应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彼此间关系的。“男人并不是故意要与你为难;他需要满足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格雷博士解释说,“而且,女人也绝不是要故意折磨你,她只是有着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欲望。”格雷还提醒我们:男人有时候需要独处,这是补充消耗殆尽的睾丸素、恢复身体健康的一种自然的途径,而女人经由谈话以及从伴侣那里得到的支持,就能够制造出减轻个人压力的荷尔蒙物质——催产素。火星人和金星人曾经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今天,他们携手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面对的是一个更加繁忙,几乎全然以工作或职业为人生导向的世界,这使得他们的情感关系也远比过去复杂得多,紧张得多,工作和生活压力也大得多。更为糟糕的是,大多数男人和女人均未意识到,男女对于压力不同的处理方式往往会破坏彼此之间的感情。一种常见的情形是:疲惫不堪的丈夫下班后回到家里,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坐到沙发上看电视;而一身疲惫的妻子下班回到家里,则更期待向丈夫倾诉白天的经历和感受。这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由于他们的愿望并不一致,愤怒和怨恨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这时候,火星和金星很容易彼此相撞。格雷博士以最前沿的情感心理学研究成果为基础,提供了一整套清晰、简洁、容易理解的情感问题解决方案,在火星和金星这两个星球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沟通和理解的桥梁。只要运用他推荐的行之有效的交流和沟通策略,就可以降低伴侣双方的压力水平,促进亲密程度。本书能够同时为男人和女人(不管单身还是已婚)带来帮助,它告诉我们,在一个以职业和工作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中,如何正确理解我们和伴侣各自应当承担的全新角色;它指导我们通过一系列新颖、实用的方法和手段,创造出一生的爱与和谐。
作者: 孙耀文著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简介: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系列,风靡全球的心理自助读物,畅销1.4亿册。 火星人金星人 长相厮守:男女持续爱恋的秘诀。 永远的距离,永远的爱人,2007年修订版。 解密两性情感密码,长踞《纽约报书评》畅销书排行榜。 亚马逊网上评论 约翰·格雷在帮助整个美国!如果每一对夫妻都阅读此书的话,离婚率将会直线下降。正如《今日美国》文章所称:火星人与金星人的形象已深入并改变着美国人的生活。 这本书做了一项非常伟大的工作,不仅告诉了你男人和女人在思想模式、做事程序、交流方式上都非常不一样,而且给出了克服交流障碍的有效方法。当男人和女人之间变成很亲密的夫妻关系时,更需要意识到双方的心理差别和相互尊重对方的自然需求、期望和梦想。 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男人和女人明明用同样的语言,说同样的词汇和句子,但他们各自想表达的意思却如此不同。这书就像一本两性用语词典,帮我们做了很多“翻译”的工作。它使我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观察男人和女人,写得非常幽默,的确太棒了! 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心理自助读物,当我读到一半的时候,妻子问我怎么样。我唯一的反应就是这本书没把我们的名字写对。我简直不敢相信格雷博士是如此准确地描述了我和我妻子这将近37年的经历和对话。 这本书太神奇了,几乎解释了我以前和先生经历的每一次分歧和冲突。读完这本书,我才深刻地理解为什么我的第一次婚姻走向了灭亡,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理解对方的需要。 约翰·格雷让我们知道男人和女人是来自于不同星球的,男女之间在心理情感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火星人和金星人的形象已经永远留存在我们生活的词典里了。
出版社:中国宇航出版社 2015-5-1
简介: 在人类探索空间、征服宇宙的历史长河中,苏联/俄罗斯一直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并作出了巨大贡献。苏联/俄罗斯的空间开发是人类空间探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创造了诸多“第一”: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奠定了现代火箭理论;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世界上第一个月球探测器及第一个登陆月球的人造物体(月球1/2号);首个行星探测器(金星1号);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轨道飞行的人(尤里?加加林)和第一位太空行走之人(阿列克谢?列昂诺夫);第一座载人空间站(礼炮号),等等。当然,其中也不乏失败的苦涩。本书即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视角,详细介绍了苏联/俄罗斯行星探测(主要是火星和金星探测)的历程:艰难起步后的高潮和低谷;伴随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科学家的喜悦与泪水。书中对20世纪初期及中叶苏联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和苏联科学家的早期活动,二战前后及冷战大背景下美/苏竞争对苏联月球与行星探测项目的影响,苏联/俄罗斯几代行星探测器几经周折的设计方案、所获科研成果,以及历次失败均有详尽而独到的描述与分析。 相信本书能对我国从事行星科学研究、行星探测器研制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起到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作者: 韦斯利·T·亨特里斯
出版社:中国宇航出版社 2017年06月
简介:
本书描述了20世纪苏联机器人探索月球及其他行星的历史。自1958至1996年,从苏联*次尝试将航天器发射至月球到俄罗斯*后一次深空发射任务,本书对这段时期所有执行的相关任务做了一个全面、精确的描述,所有组装上了发射台并意欲发射的任务都包含在其中。
【目录】
目录
第1篇 组成部分——人物、机构、火箭和航天器
第1章 太空竞赛
1.1率先抵达月球,率先抵达金星,而且率先抵达火星第2章关键人物
第2章 关键人物
2.1简介
2.2部长
2.3苏联太空计划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师
2.4苏联科学院院长
2.5设计局的首席设计师和负责人
2.6科学研究所负责人第3章主要机构
第3章 主要机构
3.1党组织,政府及军方
3.2设计局
3.2.1 OKB1
3.2.2 拉沃契金设计局
3.3科学院及其研究机构
3.4发射场
3.5通信及跟踪设施第4章火箭
第4章 火箭
4.1苏联火箭的早期研制
4.2冷战时期竞相制造洲际弹道导弹
4.3R7洲际弹道导弹和Sputnik人造卫星
4.4R7E和早期的月球探测器
4.5R7M:闪电号月球及行星运载火箭
4.6质子号运载火箭
4.7N1探月火箭第5章航天器
第5章 航天器
5.1月球航天器
5.21958—1959年:月球Ye1系列
5.31959—1960年:月球Ye2和Ye3系列
5.41963—1965年:月球Ye6系列(OKB1)
5.51966—1968年:月球Ye6M系列
(拉沃契金设计局)
5.61969—1976年:月球Ye8系列
5.71967—1970年:月球联盟号(探测号)
5.8星际航天器
5.91960—1961年:火星1M(Marsnik1)和
金星1VA
5.101962年:火星/金星2MV系列
5.111963—1972年:火星/金星3MV系列
5.121969年:火星69号航天器
5.131971—1973年:火星71号和火星73号系列
5.141975—1985年:金星/维加系列
5.151988—1996年:火卫一和火星96号航天器
第2篇将各组成部分组合在一起——飞向月球、金星,以及火星
第6章脱离地球
6.1时间线:1958年8月—1960年9月
6.2Ye1月球撞击航天器系列:1958—1959年
6.2.1计划目标
6.2.2航天器
6.2.3有效载荷
6.2.4任务说明
6.2.5结果
6.3Ye2和Ye3月球飞掠系列:1959—1960年
6.3.1计划目标
6.3.2航天器
6.3.3有效载荷
6.3.4任务说明
6.3.5结果第7章飞向火星和金星
第7章 飞向火星和金星
7.1时间线:1960年10月—1961年2月
7.2首次飞向火星:1960年
7.2.1计划目标
7.2.2航天器
7.2.3有效载荷
7.2.4任务说明
7.2.5结果
7.3*次飞向金星:1961年
7.3.1计划目标
7.3.2航天器
7.3.3有效载荷
7.3.4任务说明
7.3.5结果第8章新航天器,新的失败
第8章 新航天器, 新的失败
8.1时间线:1961年8月—1962年11月
8.2更好的航天器——第二次尝试飞向金星:1962年
8.2.1计划目标
8.2.2航天器
8.2.3有效载荷
8.2.4任务说明
8.2.5结果
8.3首个火星航天器:1962年
8.3.1计划目标
8.3.2航天器
8.3.3有效载荷
8.3.4任务说明
8.3.5结果第9章又是失败的三年
第9章 又是失败的三年
9.1时间线:1963年1月—1965年12月
9.2Ye6月球着陆器系列:1963—1965年
9.2.1计划目标
9.2.2航天器
9.2.3着陆器有效载荷
9.2.4任务说明
9.2.5结果
9.3新型航天器和飞向火星的再次尝试:1963—1965年
9.3.1计划目标
9.3.2航天器
9.3.3有效载荷
9.3.4任务说明
9.3.5结果
9.4第二个飞向金星的航天器:1964年
9.4.1计划目标
9.4.2航天器
9.4.3有效载荷
9.4.4任务说明
9.4.5结果
9.5两次令人失望的金星任务:1965年
9.5.1计划目标
9.5.2航天器
9.5.3有效载荷
9.5.4任务说明
9.5.5结果第10章*终获得月球和金星的成功,但火星仍未成功
第10 章 *终获得月球和金星的成功, 但火星仍未成功
10.1时间线:1966年1月—1968年11月
10.2Ye6月球着陆器系列:1966年
10.2.1计划目标
10.2.2航天器
10.2.3有效载荷
10.2.4任务说明
10.2.5结果
10.3Ye6绕月轨道飞行器系列:1966—1968年
10.3.1计划目标
10.3.2航天器
10.3.3有效载荷
10.3.4任务说明
10.3.5结果
10.4金星任务的首次成功:1967年
10.4.1计划目标
10.4.2航天器
10.4.3有效载荷
10.4.4任务说明
10.4.5结果
10.5探测号绕月系列:1967—1970年
10.5.1计划目标
10.5.2航天器
10.5.3有效载荷
10.5.4任务说明
10.5.5结果第11章在“阿波罗”影响下的机器人成就
第11章 在 “ 阿波罗” 影响下的机器人成就
11.1时间表:1968年12月—1970年4月
11.2金星的后续活动:1969年
11.2.1计划目标
11.2.2航天器
11.2.3有效载荷
11.2.4任务说明
11.2.5结果
11.3YE8月球漫游车系列:1969-1973年
11.3.1计划目标
11.3.2航天器
11.3.3有效载荷
11.3.4任务说明
11.3.5结果
11.4N1月球任务系列:1969-1972年
11.4.1计划目标
11.4.2航天器
11.4.3任务说明
11.4.4结果
11.5针对火星的一项大胆的新计划:1969年
11.5.1计划目标
11.5.2航天器
11.5.3有效载荷
11.5.4任务说明
11.5.5结果
11.6YE85月球样本返回系列:1969-1976年
11.6.1计划目标
11.6.2航天器
11.6.3有效载荷
11.6.4任务说明
11.6.5结果
第12章在月球、金星和火星着陆
12.1时间线:1970年8月—1972年2月
12.2抵达金星地表:1970年
12.2.1计划目标
12.2.2航天器
12.2.3有效载荷
12.2.4任务说明
12.2.5结果
12.3火星的*个着陆器:1971年
12.3.1计划目标
12.3.2航天器
12.3.3有效载荷
12.3.4任务说明
12.3.5结果
12.4YE8月球轨道器系列:1971—1974年
12.4.1计划目标
12.4.2航天器
12.4.3有效载荷
12.4.4任务说明
12.4.5结果
第13章 金星航天器、 月球火箭及陷入困境的火星任务
13.1时间线:1972年3月—1973年12月
13.2在金星地表的科研:1972年
13.2.1计划目标
13.2.2航天器
13.2.3有效载荷
13.2.4任务说明
13.2.5结果
13.3火星任务大规模失败:1973年
13.3.1计划目标
13.3.2航天器
13.3.3有效载荷
13.3.4任务说明
13.3.5结果
13.4苏联火星任务的中断:1974-1988年
第14章 从月球和火星转向金星
14.1时间线:1974—1976年
14.2一种新型的、精密复杂的金星着陆器:1975年
14.2.1计划目标
14.2.2航天器
14.2.3有效载荷
14.2.4任务说明
14.2.5结果
第15章 重复在金星的成功
15.1时间线:1977—1978年
15.2金星钻探:1978年
15.2.1计划目标
15.2.2航天器
15.2.3有效载荷
15.2.4任务说明
15.2.5结果
第16章 重返金星
16.1时间线:1979—1981年
16.2发回金星地表的彩色图像:1981年
16.2.1计划目标
16.2.2航天器
16.2.3有效载荷
16.2.4任务说明
16.2.5结果
第17章 再次返回金星
17.1时间线:1982—1983年
17.2揭开金星的云雾面纱:1983年
17.2.1计划目标
17.2.2航天器
17.2.3有效载荷
17.2.4任务说明
17.2.5结果
第18章 国际哈雷彗星活动
18.1时间线:1984—1985年
18.2金星哈雷彗星活动:1984年
18.2.1计划目标
18.2.2航天器
18.2.3有效载荷
18.2.4任务说明
18.2.5在金星领域的结果
18.2.6在哈雷彗星领域的结果
第19章 对火星及其卫星火卫一的又一次尝试
19.1时间线:1986—1988年
19.2重返火星:1988年
19.2.1计划目标
19.2.2航天器
19.2.3有效载荷
19.2.4任务说明
19.2.5结果
第20章 *后的努力: 火星 96 号
20.1时间线:1989—1996年
20.21996年大伤元气的火星任务
20.2.1从火卫一到火星96号的曲折历程
20.2.2火星96号活动目标
20.2.3航天器
20.2.4有效载荷
20.2.5任务说明
20.2.6结果
第21章 苏联月球和行星探测遗产
21.1历史概述
21.2好事、坏事和悲伤的故事
21.3继承宝贵遗产,开启新的旅程
附录A早期航天器的“尾号”
附录B苏联月球和星际航天器系列
附录C1苏联的月球任务记录
附录C2联盟号航天器的自动试验
附录C3美国机器人月球任务记录
附录D1苏联火星任务记录
附录D2美国火星任务记录
附录E1苏联金星任务记录
附录E2美国金星任务记录
附录F20世纪太空探测的里程碑事件
附录G20世纪行星探测任务时间表
附录H1苏联月球和行星探测器的着陆点
附录H2苏联火星探测器的着陆点
附录H3苏联月球探测器的着陆点
参考文献
作者: 夏景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11
简介: 一本两性和谐相处、保持美满婚姻的“幸福书”世纪佳缘1600对爱侣携手成功的秘密 “火星男和金星” 中国版第1书著名情感达人苏芩、陈彤、鱼顺顺、连谏、巫昂、黄佟佟 倾情推荐爱情保鲜秘密:尊重男女有差异,放手更幸福当当网 卓越网 新浪读书 搜狐读书 腾讯读书 凤凰网 人人网 支持好命自己修,幸福早点名著名情感作家夏景的“爱情保鲜术”这是一本关于两性差异、爱情保鲜、温情相处的“幸福书”,著名情感作家和媒体人苏芩、鱼顺顺、连谏倾情推荐。《差异的爱情才保鲜》从女性心灵成长的视角,全方位渗透了作者多年对婚恋问题、爱情真意的心得;主题涉及当下社会非常关注的相亲、网恋、两性相处、家庭烦恼、情感危机、小三、出轨、幸福婚姻等问题;重点探讨了两性相处中的诸多差异和保鲜方法,提出了最温情的解决之道,能够帮助无数女性找到自尊和自信,寻回获得幸福心灵的密码。全书文字细腻优美,充满智慧和幽默,轻松淡雅,犹如一杯沉香咖啡
作者: 寒木钓萌
简介:
寒木钓萌*的《日心大冒险》中,为了保卫地球,唐猴沙猪和寒老师准备驾驶追击号飞船飞往太阳系边缘。**站他们要去的是太阳,在接近太阳的过程中,日冕、日珥、太阳黑子……平时难得一见的太阳奇观依次展现在他们眼前。进入太阳内部后,飞船颠簸不停,怪事连连。*让他们头疼的是,太阳神不请自来,钻进了追击号,还召集恒星众神办起了星光大赛。哪颗恒星会摘得星光大赛的桂冠?不可一世的太阳神会是*后的赢家吗?离开太阳后,他们又造访了水星和金星。这两颗行星有哪些奇特之处?它们的环境有什么不同?为了满足八戒见嫦娥的愿望,同时顺便从月球上观察地球,唐猴沙猪和寒老师一起来到月球。在那里,他们不仅了解了为什么脚印能在月球上保持原样上千万年,还了解了月球怎样自转以及月球对地球的影响等天文知识。
作者: 十一点零五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8年06月
简介:
本书介绍了太阳系各大行星、彗星、流星以及星云、星系等相关的基本知识,配备了恒星的展示、太阳系的构成、十二星座,以及太阳、地球、月球、水星和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的结构展示10个AR,你可以坐在家里玩转八大行星,让地球在你指尖转动,在璀璨星空中寻找星座,并近距离观看日食与月食的奇观……在趣味阅读中了解科学原理。
简介:1.歌德:“月亮耽误了我的分娩……” 伟大的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在他的著名自传《诗与真》 的开头一段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出生: 1794年8月28日上午,时钟刚敲十二下,我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降生 了。我出生时星辰的位置是吉利的:太阳位于处女座内,正升至天顶;木星 和金星和善地凝视着太阳,水星也不忌克,土星和火星保持不关心的态度, 只有那时刚团圆的月, 因为正交它的星时,冲犯力显得格外厉害。月亮因 此耽误了我的分娩,等到这个时辰过了,我才得以诞生。 作为一位划时代的诗人,歌德的伟大自然是毋庸置疑的,恩格斯就曾经 说过,他是“真正的奥林匹亚神山上的宙斯”。这样的一个被人誉为神的人 ,在以五十九岁的高龄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果然就从自己身上发现了某 种仿佛天纵的神性。为了使这种神性得到更好的揭示,他便选用了上述雄伟 的笔法来述说自己的出生,为其自传定下基调。在歌德看来,他自己的降临 人世显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它首先而且主要与宏大的宇宙及这宇宙中 与渺小的人类关系密切的几颗星球有关,而不是与生养他的父母及家庭有关 。 穷究歌德自述的这些名堂到底是否真实是没有意思的,有意思的是这种 说法背后所隐藏的述说者个人的心理状况与真实动机。作为一位追求人的解 放、深刻展示了人类精神的伟大之处的大诗人,歌德的确有他渺小的一面。 他迷信占星术,经常谈论占梦和预感如何灵验,曾经把拿破仑、拜伦等伟大 人物的出现和他自己的某些行动与成就归因子某种超自然的,不可捉摸、不 可解释的“精灵”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歌德的智力实在不见得比普通的贩 夫走卒有更多的优越之处。据说,他刚生下来时处于“假死”状态,长时间 不哭不叫,经过多方努力才被救活过来。歌德的父母一共生了六个孩子,除 长子沃尔夫冈(即诗人歌德)和次女科内里娅之外,其余四个都不幸早夭。弟 弟妹妹们接二连三地死去,这一事实即使不曾在幼年歌德的心中造成深刻的 印象,但当诗人晚年在一种功成名就的喜悦中坐下来,着手撰写自传时,回 想起自己生命之始的死里逃生经历,他不可能不深感侥幸和惊奇。将自己的 幸运和早夭的弟妹们的不幸两相对照,对“魔法”有着浓厚的兴趣的歌德便 不免寻找和追索使自己幸运的“魔法”。在上引一段之后,《诗与真》接下 去写道:“这些吉兆——后来占星者们认为对我有很大好处——也许就是我 能活下来的原因。” 事情还不只是仅此而已。在《涛与真》中,我们见到了一个将伟大人物 的出生“戏剧化”、赋予某种非同寻常的意义的典型例证。在通常情况下, 这类事情是由那些试图通过讲述伟人故事达到自己的某种特定目的的人,或 者那些深深地为伟人的巨大魅力所震慑的传记作者来完成的,但在这里,伟 人歌德亲自动手,来对自己进行涂抹装扮了。歌德说,他的“假死”虽然使 自己家里的人大费手脚,“但结果却有利于本市的居民”。怎么个有利法呢 ?原来他的外祖父是法兰克福市的市长,这位市长鉴于外孙出生时的惊险, 从此就雇用了一位产科医师,“灌输助产的知识,或把这种知识重新讲求起 来”,使得该市此后出生的小孩大受裨益。 不管事实本身究竟是怎样的,读过这些自述之后,我们难免会得到这样 一种作者本人或有意或无意希望我们得到的印象,即:伟人歌德的伟大程度 虽然不会因为这样一桩小小不言的事情而有所增加,但他的“伟大性”却是 在他降生人世之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的。 这显然是一种假象。刻意制造这种假象,对歌德本人而言,只不过进一 步印证了恩格斯对他所作出的著名评论:“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 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社会并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 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但是对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类似的假象在他 们逐渐确立自己的世界观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影响却可能是灾难性的。一方面 ,它们可能起到强化伟人是与常人绝对不同、毫无干系的“特殊材料制成的 人”这一错误观念的作用,易于导致对伟人的盲目迷信和个人崇拜;另一方 面,它们易于造成思想混乱,打击青少年的上进心,使他们产生较为深刻的 自卑感,甚至完全放弃自我完善的努力。
作者: (英)拉曼普林贾 吴霖译
简介:你知道怎样找到北极星吗?这样你就再也不会迷路了。怎样通过熟悉的指路星找到狮子座呢?怎么去预测月亮的相位以及理解它们发生的原因呢?要怎么做才能安全地观看日食流星雨能够点亮天空,但何时何地你能看到它们呢?……夜空中充满了新奇和迷人的景象。只要一些装备和这本书,你就可以用你的双眼去探索宇宙奥秘。超清晰细腻星空彩图和顶级天文学家权威解读,指导你学习使用专业工具,甚至学会用肉眼,找寻、识别并观测到夜空中的神秘天体。从古老的恒星穿梭到稍显年轻的行星,从令人神往的星座飞跃到让人惊叹的天文奇观,让你亲身感受到绚丽多彩的灿烂星空。你可以知晓恒星的名字以及它们在天空中组成的图案,你还可找到超巨星以及恒星诞生的地方;你也可以探索月球上的环形山、高地、月海以及绕着木星转动的巨大卫星,你还可以躺下观看如烟花般绚烂的多姿多彩的极光。那你还等什么呢?快跟我们一起踏上奇妙的星空之旅吧!《黑夜天文观测》(精装典藏版)是从英国儿童百科权威出版公司QED引进出版的权威天文科普巨作,超清晰震撼星空彩图和顶级天文学家权威解读,指导读者找寻、识别并观测夜空中的神秘天体,带领读者去探索这迷人的宇宙。主要内容清楚恒星的运动规律,并弄明白为何恒星和星座会在晚上一直出现;为了舒适而安全地观察神秘而美丽的夜空,你首先应明确自己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去解开有些恒星看起来明亮而鲜艳,其他恒星却黯淡无光的谜题;了解恒星、行星和太空其他物体之间的差异。牵星法观察夜空时通过熟悉的指路星找到星座;探索星座并描绘夜空下星座像动物或英雄般的外形;在星座间用牵星法找到遥远的恒星和星系,巨大的尘云以及其他外来物体;知晓恒星和星座的名字;学习怎么找北极星,以后你再也不会迷路了。行星看看内行星水星和金星的相位;找找是什么原因让火星变成了一颗红色的星球,土星环又是由什么构成的;了解行星的轨道以及它们是如何对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景象产生影响的;行星是怎么形成的,它们是由什么成分组成的?去发现观察夜空中行星的最好时间。月球 在夜空下观测最大而且最亮的卫星——月球,了解它是什么时候且如何形成的;一个月内月亮的形状看起来是在不断改变的——了解怎么去预测月亮的相位以及理解它们发生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只能看到月球亮的一边?找到月球暗的那一边,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观测月球的表面,并认出它表面的环形山和海洋特征;找到航天员探测月球时的登陆点。不寻常的景象日食是个奇怪的景象——看看它是怎么发生的,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发生,并想想要怎么做才能安全地观看日食;流星雨能够点亮天空,但是何时何地你能看到它们呢?彗星是什么?你何时能看到一次?来学习更多有关这些冰球的知识吧;太阳风是通过什么手段使我们的大气层发亮的呢?找到流星和陨石的区别。
作者: (英)卡佳坦·波斯基特(Kjartan Poskitt)原著;(英)丹尼奥·波斯盖特(Daniel Postgate)插图;阎宝华译
出版社: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
简介:0 非常明亮的星星。 -1.6 这是天狼星的星等,它是天空中最明亮的恒星。 -4.4 这是金星的最大星等。 -12.5 这是满月的星等。 -26.7 这是太阳的星等。 ·从地球上看,天狼星似乎是天空最明亮的星星,因为天狼星距离我们很近——只有8.5光年。其他星星远比天狼星发光能力强(比如猎户座中的参宿七),但是,因为它们离我们非常遥远,所以看上去不那么明亮。 怎样寻找籽量 由于行星是在天空中运行着的,所以要把它们标在星图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事情也有例外。每年总有人印刷各种各样的“历书”和图表,其中最好的一本小册子叫《星空时代》。这本书中有一幅星图,特地标出了当年每个月行星出现的位置,还告诉我们月亮将运行到什么位置,以及是否会出现好看的月食等等. 如果你自己能够独立找到行星的准确位置,那可真是开心哪!一旦你熟悉了不同的星座,就可以仔细看一看哪个星座中突然多出了一颗星。(一定要弄清楚它不是飞机,也不是飞碟或其他什么物体。)这颗星不是恒星,肯定是一颗行星! 因为行星有自己的运行轨道,所以,有时候几个星期一颗行星也看不到,可有时候,你可以同时看到好几颗行星。 内行墨 水星和金星被称为内行星,这是不是意味着它们地位低下,连金鱼都可以对它们发号施令?不是的,这个称呼仅仅是指它们比地球离太阳更近。由于靠近太阳,它们整个儿白天都挂在天空中。但是,白天太阳光非常强烈,致使它们几乎不可能被人们看到。当然,当它们处在一定的位置上,我们有时的确能够在日出前或日落后的一小段时间内看到它们。 如果水星和金星在运行中达到与太阳处在一条直线的位置上,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到它们。(与太阳处在一条直线上称为“合”。) 在这幅图中,水星位于太阳和地球之间,也许你会认为我们应该能看到它。实际上,就像你在汽车远光灯下去找一粒沙子一样,这时你是不可能找到水星的。 当水星和金星处在太阳的同侧或者两侧,我们就可以在早晨太阳升起之前或者傍晚太阳刚刚落山之后看到它们。 即使在观察的最好季节,我们也只能在日出前或日落后两小时内看到水星。不幸的是,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它非常小,而且经常接近地平线。(观察天空中位置很低的东西很困难,因为地表附近空气流动不定,往往使小东西变得模糊不清。) 金星到太阳的距离比水星远,因此我们可以在日出前或日落后3个小时内看到它。在大多数月份里,无论是在早晨